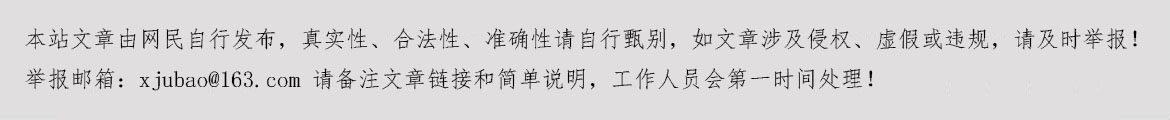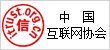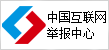作者谌容离世,她的作品引发全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
2024-02-05 20:26:31
曾写下《人到中年》的作家谌容走了。据北京市文联,作家谌容因病医治无效,于2024年2月4日在京去世,享年88岁。根据逝者生前愿望,丧事从简,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,不举行追悼会和任何形式的追思会,家中不设灵堂。
谌容是著名作家、编剧,也是梁左、梁天、梁欢的母亲。上世纪70年代她开始文学创作,1975年出版个人首部长篇小说《万年青》,1978年出版长篇小说《光明与黑暗》。1979年中篇小说《永远是春天》发表在巴金先生担任主编的《收获》杂志上,茅盾先生对该作品点名称赞,称其为“中篇小说出现了初步的繁荣”的代表。
谌容一生创作丰厚,出版的作品还有小说《减去十岁》《懒得结婚》等,收录于《谌容文集》。
1980年,谌容发表中篇小说《人到中年》,迅速引发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。
巴金、孙犁等一批大家对她白沟河加工网 白沟河网 白沟河网最新接加工 白沟河网最新放加工 图文印刷网的小说交口称赞,黄永玉主动给她的作品插画。这篇小说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一等奖,被评为“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有影响力的40部小说”之一,同名电影荣获第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第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,谌容本人也凭借该片荣获第5届小百花奖优秀编剧奖。
据报道,《人到中年》发表后不到一年时间里,就催生了二三十篇评论文章。1980年3月26日的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丹晨的评论《一个平凡的新人形象》。文章称赞《人到中年》塑造了一个感人肺腑的艺术形象——陆文婷。北京市文联发布的讣告也写到,谌容敏锐地触及了一个富于时代意义的社会问题,显示了其艺术良知与勇气,引发了全社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视。
1981年,《收获》杂志在莫干山举办笔会,巴金参加,谌容、张辛欣、吴强、叶蔚林、冯骥才、汪浙成等一批当时风头很健的中青年作家相聚于夷白楼,在浙江土地上留下了文学足迹。
2017年,《收获》6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,谌容回忆,她已经很久没有给《收获》投稿了,“我记得巴老讲过一句话,作家的名字应该署在作品上。参加这个会我挺突然的,我也很纠结来不来,最后还是特想来就来了,主要是为了看看老朋友,另外我想去巴老的纪念馆祭奠一下巴老。我和《收获》的关系益师益友的关系,在我是业余作者的时候,我的第一本作品《收获》发的,在2007年我的最后一个中篇也是《收获》发的。我对《收获》当然是很有感情的,我认为在现代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,一个刊物能够存活60年非常不容易,尤其是《收获》,因为《收获》是一个纯文学刊物,它不媚俗,不跟风,也不拜金,所以我很尊重这个刊物,我也愿意跟这个刊物有很密切的联系,把我的作品给他们。我的责任编辑是李小林,比我小10岁,但是我觉得她眼睛特别尖,在我最初的作品,比如说《人到中年》,我写到四分之一,那时候我还是业余作者,她看了以后给我提了一些意见,然后修改,很多稿件都是《收获》的编辑帮我提出很宝贵的意见,所以我觉得《收获》是帮助了一批作者,推出了很多好作品,我是没有黄永玉老师的勇气,94岁还敢写东西,我现在比他小十几岁,82岁,但是我已经写了东西放在电脑不敢拿出来,我觉得好像不够水平。”
2019年,谌容84岁那年,接受《光明日报》采访,记者以《谌容:以我笔写我心》发稿,写到,“见面的这天,她凌晨2点睡的,起床时已中午12点。起床后,她一边坐在沙发上听古筝曲,一边摆弄着手提电脑看看股市行情。见面约在下午3点——股市停盘的时间。这犹如年轻人的作息是84岁的谌容“随心所欲”的日常。”
以下是《谌容:以我笔写我心》全文:
84岁的她,曾写下《人到中年》。巴金、孙犁等一批大家对她的小说交口称赞,黄永玉主动给她的作品插画,但即使在最火的时候她也鲜少将自己暴露在公众视野中。巴金曾说:“作者的名字应该署在作品上。”她非常赞同,并严格遵守。
见面的这天,她凌晨2点睡的,起床时已中午12点。起床后,她一边坐在沙发上听古筝曲,一边摆弄着手提电脑看看股市行情。见面约在下午3点——股市停盘的时间。这犹如年轻人的作息是84岁的谌容“随心所欲”的日常。
谌容曾经写下《人到中年》。中年时,她已是最知名的女作家之一。巴金、孙犁等一批大家对她的小说交口称赞,黄永玉主动给她的作品插画。可即使在最火的时候,她也鲜少将自己暴露在公众视野中,近年来更是近乎消失了。巴金曾说:“作者的名字应该署在作品上。”她非常赞同,严格遵守,尽量谢绝采访、上封面、上镜头、介绍写作经验。能见到她的原因,一定与作品有关——她的六卷文集即将出版。
成套的文集她没出过,这一次也是在老朋友们的大力“鼓动”下,出版社积极联系,才有此一套。“我跟出版社说,出我的文集要赔钱的。”谌容朗声笑说。舒展的面容,利落的短发,看得出年轻时做演员也足够的美貌,而曾经标志一样的黑眼圈看不出了。
黑眼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身体不好。年轻时因为原因不明不时发作的晕厥,她从中央广播事业局被调到教师岗,最后被放了病假。细腻的情致、好胜的性格、对文学的喜爱和因病而来的宽裕时间,将她推到了写作的道路上。
曾经她病到没有力气为自己的选集写一篇不足千字的序言,但这样的身体里蕴含的能量惊人。
在20世纪60年代的特殊岁月,她一边下放劳动一边“秘密”在油灯下忘我地写作。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,写出的长篇小说不允许出版,她愤而为自己争取权利。
70年代末,社会思潮尚在摇摆,知识分子在文学中还是“被改造者”的形象,她以知识分子的担当写知识分子的处境,敏锐触及了当时十分敏感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。对这个群体的“理想、志趣、甘苦和追求”、他们内心深处的感情她理解得透彻、表达得传神。她自认并没有考虑要“揭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”,只是根据生活中的感受,“不用刻意体验、收集,身边全是知识分子”。
《人到中年》引起了全社会的大讨论,时而赞誉有加,时而开会批判。掌声和批评,她照单全收,然后继续坚持以我手写我心。
“每走一步都是‘置之死地’而又起死回生。”诚如她所说,年轻的人已经难以感受这份坚韧、认真可能会招致怎样的灾难,但不难感受到她对写作的珍视更甚于个人安危。
这份珍视,使得她在那个粗粝的、去个人化的年代,保留着斗争的勇气。同样被保护着的是自己作为人的真心、作为作家的敏感。
如今虽然体力无法满足创作的需要了,可这份敏感仍在。
她随口聊起一部20世纪90年代写的电视连续剧《懒得结婚》,笑称“没什么反响”,可电视剧中的现象如今已经得到印证。
这也许来自于她总是乐于接受新鲜事物。西方哲学思潮传入中国,她研究萨特的思想,写了一本小说叫《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》;写作的工具1993年就换成了电脑;写书法、画画是她的爱好,可也不耽误她现在玩儿微信、刷朋友圈、吃烧烤、网购。
尽管时光在她身边流逝得似乎慢了下来,但这个身体已经做过三次手术:心脏装了两个支架,胆摘了,脊柱也动了大手术。被改变的还有点其他什么。
曾经,她作为一个作者,“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读者喜爱自己的作品”。如今她也淡然了,“忘了我就忘了吧”。作为一个反映人生和社会问题的作家,她心里很清楚,“社会的问题已经变了,下一代人永远在叛逆上一代人,因为时代在发展,要承认这一点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欢。我作为一个作者,尽到了自己的责任,非让人家看我的小说,没道理。”